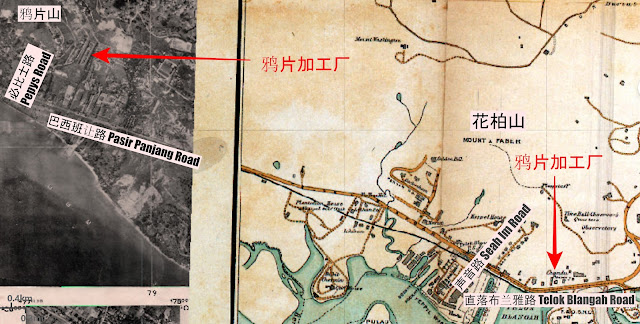2024年10月,搭乘东方航空,晚上抵达杭州萧山机场,从下机到出闸费时约一个小时。通过Agoda预约的车子早在机场等候,45分钟后抵达绍兴柯桥富丽华酒店。酒店也是在Agoda预订的。
北国秋天,没有必须穿上风衣那种秋天的感觉。
轻纺城地铁站距离下榻酒店只有百米之遥,接下来三天的绍兴行程,地铁和滴滴成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,巴士则搭过一回。在Alipay下载绍兴公交卡,地铁(Metro)和巴士都可通行,比起广州只限搭乘地铁要有人情味得多。
鲁迅故里
酒店含早餐,反正是自由行,从容地用过早餐,从轻纺城地铁站直达鲁迅故里。
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是杰出的,对新青年产生一定影响力,他的著作亦受到日本文艺界的追崇。出于政治目的,他的个人形象变成中国红潮的神话,神位远远超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家,杰出的教育家如蔡元培,以及将一生投入社会改革的周恩来。鲁迅接受林文庆的聘请,在厦门大学只教了三个月课便因理念不同而拂袖而去,厦大展馆内以大篇幅讲鲁迅,当了16年校长的林文庆只是点到为止。
民国初年,鲁迅举家迁往北京,将屋子连同后院(百草园)卖给富豪邻居朱阆仙。朱家将偌大的产业拆建,其中三间没什么改动,正好保存部分鲁迅故居。
鲁迅家道中落的原因,是因为他的祖父向江苏主考通关节,被苏州知府发觉,被押刑部狱七年,周家所有的钱都在这七年中花得七七八八,故居因此衰落。
鲁迅故里细分为鲁迅祖屋、鲁迅故居、三味书屋,以及鲁迅纪念馆,主要根据鲁迅的文字描写来还原。我们景仰的是鲁迅的文学,放下文学作品,鲁迅故里是个商业打卡区,想象中的人文气息几乎被不守规矩,抽烟吐痰,大声叫嚷,只为沾个文化光环的内地游客破坏了。更可怕的是,还没到闭馆时间,工作人员已经催促众人离开。大门一锁上,他们骑着电瓶车,在不可通车的步行街上一路按响喇叭抢路。若鲁迅活到今天,他会如何下笔批判?
三味书屋是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故居中的一间,现在整个寿宅都开放。三味书屋还原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所描写的格局,文中写道:“出门向东,不上半里,走过一道石桥,便是我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,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匾道:三味书屋;匾下面是一幅画,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,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,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” 当时念私塾的学生,都是自己买好桌椅带去的,鲁迅的课桌放在角落。
如今百草园连同朱家并入鲁迅故居,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的百草园是什么?“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,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(朱熹)的子孙了,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,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;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”
鲁迅故居看不到闰土的影子。《故乡》的闰土是童年的玩伴,“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”,多年以后“一见便知道是闰土,但又不是记忆上的闰土了”。闰土叫他“老爷”。…
看到鲁迅故居内摆设的摇椅,对鲁迅元配朱安多了解一些。朱安是名封建传统女性,目不识丁,缠足、精于缝纫烹饪、性格温顺。这是由母亲安排的婚姻,鲁迅不喜欢朱安,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时认识的学生许广平自由恋爱,同居育儿。在绍兴老家和北京,他都避免和朱安见面。朱安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婆婆,其余时间或许就是坐在摇椅上独守空闺,一摇一华年,度过一辈子有名无实的婚姻。如果她嫁入另一个守旧的封建家庭,日子是否好过些?
我的中学华文课本收录鲁迅的《风筝》和《秋夜》,课余阅读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故乡》和丰子恺插图的《阿Q正传》。至于鲁迅与元配朱安只字不提,只知道鲁迅与学生许广平共谱恋曲。
上世纪70年代初,新加坡文团受到中国文革影响,纷纷组织学习小组,通过学鲁迅来提高伙伴的思想水平。《海洋文艺》第二卷第十期(1975年10月号)内容重点是“鲁迅纪念专辑”,当时鲁迅去世39年,通过“鲁迅评水浒”、“鲁迅怎样教导美术青年”、“鲁迅小说的艺术”等来推动读者研读鲁迅的著作,推荐读者阅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印的《鲁迅全集》等,对文艺知青来说,“鲁迅是我们的导师”。
新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,走现实主义道路的文艺工作者,会从鲁迅的小说、杂文中获得启发与灵感,杂文称为文艺匕首,而鲁迅写小说是从加入《新青年》编辑阵容开始的,他在《新青年》的“随感录”栏目开始用匕首式的杂文从事散文创作,杂文就是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战斗工具。1918年提倡“文学革命”开始写小说。他的《阿Q正传》至少有七八个外国译本。有人形容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。
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
运交华盖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
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。
这些诗句都是学鲁迅的年代,我在文团的学习汇报中用心记下来的。
沈园: 爱情悲歌
到了鲁迅故里,顺便到附近的沈园走走。以中国的霸气来说,沈园只能说是个小公园,荒芜多年后,1980年代振兴旅游,借南宋文人陆游的名气开始修复的。因为有故事,有文采,可以感受陆游与唐婉有情却被无情误的爱情悲歌。
陆游初娶唐婉,朝夕相对,鸾凤和鸣,因此造成婆媳关系欠佳,为了尽孝而休妻。几年后两人在沈园偶遇,唐婉已改嫁,陆游亦另娶。陆游触景生情,在墙上题词《钗头凤》 :
红酥手,黄藤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。
东风恶,欢情薄,一怀愁绪,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!
春如旧,人空瘦,泪痕红邑鲛绡透。
桃花落,闲池阁。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!
翌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看见此词,于是和一阕《钗头凤》,未几抑郁而终:
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。
晓风干,泪痕残,欲笺心事,独语斜阑。难!难!难!
人成各,今非昨,病魂长似秋千索。
角声寒,夜阑珊,怕人寻问,咽泪装欢。瞒!瞒!瞒!
陆游休妻之事,南宋刘克庄《后村诗话·续集·卷二》可能是最早的文献记载:
放翁少时,二亲教督甚严。初婚某氏,伉俪相得,二亲恐其惰于学也,数谴妇。放翁不敢逆尊者意,与妇诀。某氏改事某官,与陆氏有中外。一日通家于沈园,坐间目成而已。翁得年最高,晚有二绝云:
肠断城头画角哀,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见惊鸿照影来。
梦断香销四十年,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,尤吊遗踪一泫然。
旧读此诗,不解其意,后见曾温伯,言其详。温伯名黯,茶山孙,受学于放翁。
蔡元培故居
绍兴第三天,搭乘地铁前往城市广场(鲁迅故里前一个站),步行到蔡元培、周恩来和王羲之故居,这三个故居刚好成三角形。蔡元培和周恩来故居相对宁静,游人的素质好多了。
蔡元培眼见戊戌变法失败,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,32岁时辞官归故里,在乡下监督中西学堂,推广新知识新思想。这是新学旧学撞击的年代,旧派人士容不下中西学堂,蔡元培最终辞去职务。随着反清革命情绪高涨,蔡元培出任上海光复会首任会长,绍兴“辛亥三杰”陶成章、徐锡麟和秋瑾乃重要成员。陶成章于民国初年被暗杀,徐锡麟和秋瑾则因反清失败而就义,秋风秋雨愁煞人!
蔡元培识英雄重英雄,担任教育总长、北京大学校长和大学院院长时,都聘请鲁迅一同工作,鲁迅去世后致力推动《鲁迅全集》编印出版。
蔡元培一生有三段婚姻,元配王昭是媒妁之言,第二和第三位夫人黄世振和周峻都是自主婚姻。蔡元培崇尚一夫一妻制,续弦都是夫人去世后另娶的。蔡元培改变女子嫁夫从夫的观念,接受男女平权,妇女解放,认为夫妻之间人格平等,他也做到身体力行。
周恩来故居
周恩来,人民的总理,俯身为民众做牛做马,一生忍辱负重,被批斗又打又拉,又拉又打,还是 “顾全大局,相忍为党”,继续支撑下去。周恩来也不是个希望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,留下遗愿“平祖坟,还耕于民”。
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时,我还是先从傍晚出版的《新明日报》得到最新头条。周恩来死后火化,骨灰撒在北京长城、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入海口及山东渤海黄河入海口。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,周恩来从日本回国,积极投入爱国运动,主编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,参与发起觉悟社,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,奠定他日领导国家的基础。
1955年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,周恩来的“向在地国效忠”一席话,解开千千万万海外华人对国家认同的纠结,其中包括向来认为中国才是祖国的新加坡华人。
看到几张1960年代周恩来与青年民众的合照,估计这些昔日年轻人如今已七老八十,他们对周总理是否怀念?他们到此一游吗?对昔日的理想,今日的生活,有些什么感想?
王羲之兰亭
从蔡元培故居走过小巷子,在特色小店三已小院喝咖啡吃小点心后,续程王羲之故居“戒珠寺”。王羲之舍宅为寺有个传说,相传他喜欢鹅和宝珠,一日宝珠被鹅吞掉了,他却误会是来访的僧人手脚不干净,于是冷落这位朋友,僧人知情后想不开而自尽。几天后王羲之家中一头鹅倒地身亡,家人在鹅肚子里发现丢失的宝珠。王羲之深感僧人冤死,心中十分沉痛,从此不再玩珠,并且将住宅捐出来建寺。
据说王羲之每天勤奋写字,写完了就在旁边的水池洗毛笔。所谓日久见功,本来清澈见底的水池被洗成“墨池”,成为今天的打卡点。
我读小学的时候学习名家书法,临摹过唐朝颜真卿和柳公权,以及东晋王羲之的字帖。我们以为可在故居看到《兰亭序》,转了一圈知道来错地方入错门,连忙打滴赶往十多公里外的兰亭,闭园前终于走完兰亭。
兰亭是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的地方,日后雅集受到各个朝代上流社会所推崇,形成兴盛一时的兰亭文化。话说王羲之等42名文人雅士相聚兰亭,将盛满酒的羽觞(酒器)放入溪水中漂流,漂至谁的面前,谁就取觞饮酒作诗。若无法成诗,就要罚喝三杯。“曲水流觞”当场汇集37首诗,王羲之乘兴落笔,写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《兰亭序》。
现在看到的《兰亭序》乃临摹之作,据说唐太宗千方百计得到《兰亭序》真迹,死后还将它作为陪葬品。日后唐太宗墓被盗,并没发现兰亭序,推测藏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墓。
《兰亭序》其中一段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。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”以白话来说,就是“向上仰望,天空广大无边,向下俯视,地上事物如此繁多,这样开阔胸怀的视听享受,实在快乐啊!”
行万里路看天下,您快乐吗?
柯桥与安昌古镇
绍兴第二天的午餐在鲁迅故里的餐馆解决, 傍晚先回到酒店休息一阵子,过后到附近几座商场吃晚餐。进入外观堂皇的商场才知道什么叫做南柯一梦,这些商场只是一楼营业,其他都拉起闸门了。这才了解到绍兴不是主要城镇,冠病疫情以来,经济不景气没好转过。我们抱着大城市商场的心态走进来,未免落差太大。
最终在酒店对面的商场二楼唯一开门营业的若耶溪居酒屋解决,整个晚上只有我们四人一桌生意,直到快离开时才有两个女生走进来,点了两碗汤面。我们叫些特色日本餐点,外加一瓶日本清酒, 500元人民币可说是大交易了,其中清酒的价格占一半,店家难得做成一笔“大生意”,来个甜品大赠送。店员说绍兴本来就游客不多,可能都到鲁迅故里、柯桥古镇和安昌古镇去了。
第三晚和第四晚分别去了柯桥古镇和安昌古镇,顺便在古镇用餐。冷冷清清的古镇没有预期中的人潮。
柯桥古镇旧称笛里,内河与浙江东部运河交汇,古称柯水,柯水上建柯桥,古镇因此得名。古镇三桥包括宋代柯桥、明代融光桥、清代永丰桥,灯光映辉下每座桥都是双桥,一在水上,一在水中。话说回来,走柯桥古镇,看照片比起脚下的感觉好得多。
百度百科将安昌古镇形容为“碧水贯街千万居,彩虹跨河十七桥”,照片,照骗,在中国行走多年,体会到现实与想象往往就像看似远处相会,实际上无法相交的平行线,没到过终生遗憾,到了遗憾终生。
安昌古镇以腌制腊味闻名,当地人说年关近晚,这里特别热闹,居民纷纷涌来买些腊鸡腊鸭腊肉腊肠好过年。我们走完桥的这边,过桥走桥的另一边。停下脚步打斤黄酒吃晚餐,其中一道菜色就是当地的腊味。感觉上还是广东腊味好吃多了。